回帖2315
主题14564
在线时间9190 小时
注册时间2010-4-7
最后登录2026-3-1
我的奖状
|
马上注册,结交更多曲靖朋友,赢取金币兑换话费、礼品!
您需要 登录 才可以下载或查看,没有账号?注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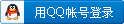
x
大理古城以北18公里的喜洲,是老舍眼中的“东方剑桥”。从这里的民宿获得的,是当地白族人的历史和民间手工艺的古朴。
摄影 :张雷
古镇寻幽
冬日午后,大理喜洲古镇外的城北村,一只猫卧在我脚边睡觉。大理的云动得快,日光也被拉着跑。猫跟着挪窝儿,不一会儿便闪进村子深处的小门里。
我追随猫的踪迹,在逼仄的院墙下,来到己已巳客栈。正在整修的村路尘土飞扬,窄门后一爿青藤撑起的小院,翠绿将灰尘滤掉,只剩暖阳点亮木屋前的一对躺椅,帆布上泛起白光。躺椅后的房间幽暗,隔过一张客床,却有一具四角有立柱、四周有雕花围栏、头顶有顶架的清代架子床,里面吊起一盏橘黄的灯。
“床是从村里淘的,觉得有意思,又没别的地方放,就放在客房里了。每个房间的布置都不一样。”老板田飞出现在院中的二层露台,帽子下是被晒得黝黑的皮肤,只有披肩的头发和四川普通话的口音,泄露出他是外乡人。不论村民、店员,都敬称他“田老师”。
成都人田飞将喜洲老宅焕然一新,成为它的新主人
猫是他的。邂逅猫前,我刚从喜洲古镇出来。那里以白族民居建筑群著称,方圆不到18公顷的面积内,当前仍有120多座完整院落。“进到镇里,仿佛是到了英国的剑桥,街旁到处流着活水:一出门,便可以洗菜洗衣,而污浊立刻随流而逝。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有图书馆,馆前立着大理石的牌坊,字是贴金的有像王宫似的深宅大院,都是雕梁画柱。”
77年前老舍觉得“体面”的小镇,现已萦绕着旅游气息。活水全无,四方街周边的街道开满售卖衣服、小吃、民间工艺品的店面。叫得上名号的院子门口挂着牌,但除却三四家有两三进院落、两层楼高照壁的大院,宏伟院落已不多。沿街随处可见高耸的白墙,小巷深处仍是夯土本色。头裹包头、身着蓝色领褂的白族老妪背着箩筐,从穿着婚纱、“钉”在古屋外的新娘身边走过。
如今的古镇更像一个图鉴。古屋的门上贴着的符纸代表什么,赋予白族姑娘包头和衣服色彩的扎染工艺怎么做,乃至老舍口中古镇“不到一里便是洱海,不到五六里便是高山”的妙处何在?惊喜都在镇外,咫尺之遥的城北村便是首选。
喜洲古镇深处,新旧房屋交错
城北村与喜洲古镇相隔一片稻田,村口是几乎与古镇本身齐名的喜林苑。从古镇走去,蓝天是一层、穷目力所及的绿田是一层、喜林苑的一排橘黄外墙又是一层。那里曾是喜洲商帮“八重家”之一杨品相的大院,由美国人林登夫妇在十多年前依建筑原貌改造成酒店和文化交流的会所。这个连着四重院落的深宅大院,既是文物保护单位,又被林登办成了外国人来此写生、游学的基地。
不过,因其规模和庄严,喜林苑像个正襟危坐的博物馆和互动的课堂,而紧挨喜林苑的己已巳客栈,更有主人松懒的气息,像是民宿的样子。而镇中所见甲马和羊毛毡的传统工艺,又都指向这个外乡人。我和田飞的猫,乃至他本人的相遇,就不是偶然。
“己已巳最初的主人是做丝绸生意的杨家,停工于己丑年(1949年),而我在癸巳年(2013年)接手,两个时间节点预示这个院子不同的命运,我取其中字形相近的两个字,中间再加个‘已经’的‘已’,便有了现在的名字。”45岁的田飞烟不离手,侃侃而谈,烟雾间不时闪过微笑,与外人口中四川美院出身的他喜好独处,似乎难以接近的印象相差不少。“以前在城北村路南,只有己已巳和喜林苑两个院子,剩下的房子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造的。”
己已巳中本镇的店员也奈何不得客栈里勾人的猫
他邀我在院中的咖啡馆落座,我们相隔的桌子是一块放平的门板,旁边的书架上摆着他写的书,土墙上则挂着他妻子的画作。他告诉我:“1999年,我辞了国企的工作,和妻子从成都出发,走了40多天,到各地看民居。当时就知道喜洲的白族民居有名,到大理古城第二天,就骑车跑到喜洲。但相比徽式建筑,这里的特点是雕梁画栋的彩绘,没有那般的高低错落之感,印象一般,便从云南回去了。直到2013年北京雾霾严重,我们来到大理,发现这里仍像世外桃源。”
大理古城的外乡人与在喜洲扎根的外来者在我看来,几乎来自不同的星球。古城的新大理人整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聚会,而在古城北方18公里的喜洲,即使多年好友,相距几百米也可能一两个月不见面。田飞亦有同感,他喜爱独处,却难以忍受城市的孤绝,爱上了这里的乡土气息。他记得那时四方街周边的店铺寥寥无几,卖的是五金零件一类本地人的生活必需品。田里仍是大家各种各的,“地里参差不齐,总有忙碌的热闹”。
“当时除了喜林苑,只有本地人开的两三家客栈。即使2016年以后旅行社入驻四方街,沿街取悦游客的店铺疯长,整个喜洲到现在也仍只有几十家客栈。”在成都长大、北京生活的田飞闯进农村,想和妻子在村里建个工作室,租住在喜林苑旁边的客栈。他们当时每天坐在四方街路边,漫无目的地找房子。回到住处时,恰好看到喜林苑背后,一个比周边房子都高一截的院子。
那里有7个房东,院内被各家分割,院落早已衰败,笼罩着霉味。6年间,房东陆续把房子交给他,除了自己住,他把院中的猪圈改成咖啡馆,把厢房做成客房,开起民宿,彻底告别了此前的生计,却与游客往来不多,反倒彻底扎进了村里。
【民宿,远方亦故乡】
民居的教义
我和田飞聊天的屋子在院子东北角木房子的二层,相当于一个避风室,外面有支起遮阳伞,由水泥铸成的露台,一层是前台和咖啡馆。院中的其他三面都是两层的木屋客房,共有6间,外表全是木头被打磨后的素色,前人在梁柱上的笔墨丹青,用深褐色的木框“装裱”起来,走廊上的桌椅不是木色就是米白色,唯有墙上彩绘斑驳。院中藤架下有鱼池,院落四角种满芭蕉和松树,茂密的叶子伸到二楼。
最初唯令我感到乏味的是一层咖啡馆旁的小陈列室,里面摆放着民国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练字本、文件,乃至上世纪60年代的奖状,以及挂在墙上的农具。乍看上去,像是衬托老院子格调的复古装饰,冗余得有些累赘。但店长杨小云却引以为傲:“那是呈现己已巳温度的地方。”杨小云来到店里将满一年,他是大理的白族人,说话时慢条斯理,眼睛发亮,“陈列的旧物都是房东留下的”。
“90后”杨小云曾在喜林苑工作过3年,经验丰富。作为店长,他负责店内日常,与客人的互动最多,会向客人介绍咖啡馆的陈设。而田飞多在自己封闭的工作室,与客人的交流很少,即便到前台来,见他与游客打招呼,平凡的装束也难以令游客想到他是老板。但杨小云来时,陈列室已经由田飞亲手布置完毕。田飞向我介绍自己的初衷,他从中拿起一个纸盒,里面是各国的扑克牌,却是清一色的大小王。“那是房东的祖父年轻时收集的。我们一位房东的父亲把自己和祖辈的旧物放在一个箱子里。收拾房间时,房东觉得这些东西可以扔了,我觉得它们能反映房主的生活,就想把它们都陈列出来,既让客人了解院子的历史,也表达对房东的尊重。”
打开客房的窗户,田园就在眼前
田飞告诉我,己已巳老宅的历史,乃至喜洲近代的过往,在整理时交织在他眼前。“这位房东的曾祖父是喜洲的县长,祖父是位喜爱书画、音乐、练武的公子。”田飞说,陈列馆里的电话和西式闹钟,都是“二战”时的产物。白族自古事耕读、重教育,明清时喜洲共出过70多名进士,而商帮的辉煌则是在抗战时期。“喜洲是美军从缅甸向内地运送物资的要道之一,小到生活用品,大到木料,运输过程中都会留下一些。喜洲大部分院子也是在那时建的。”
己已巳也不例外,梁柱乃至门窗的材料均是云南地区最好的楸木,而前人的个性不仅藏在练习本等旧物里,宅院中的彩绘里也遍布房主的手迹,杨氏先人仿米芾、唐寅、青藤、八大山人,山墙、柱头檐口,凡精巧处无不施以彩绘浮雕。极盛之时,却逢岸谷之变,杨家在“土改”中衰落。“己已巳本来应该像喜林苑一样有四进大院子,每个院内都是二层能够走通的走马转角楼,但后来没钱修,只修了一个院,连门都是后来开的小门。”田飞向我感慨。
“原先林登也想把那个院子租下来,但因为产权太复杂,后来放弃了。”一个院子出现7位房东也是源于那时的变动。当田飞初到老宅时,只有一位房东仍住在里面。房东见有人租房,闲着也无用,爽快地答应租给田飞五间房,足够他自住和工作。田飞说:“我们装修好后,其他的房东看着效果不错,又陆续把房子租给我。我看房子多,就想着做民宿。”
在田飞看来,分批拿到房屋的局限在于,东边一间,西边一栋,目前房子里仍住着一位房东,见己已巳生意不错,也在院子里开起客栈。设计难以统一,房屋改造时也难以大动,用水用电时,木房子里失火的隐患也更大,住户体验受到限制。但其实恰是产权的分割,使他只能因地制宜,成为除了喜林苑之外,喜洲唯一修复后,完整保留老房子的民宿。“本村人很喜欢我们院子的风格,客栈也只有夜里关门,经常有邻居抱着孩子上院里的池塘边看鱼。”
喜洲古镇曾经的军人服务社虽已荒废,但难得清净,如今成为游客拍照的胜地。
我在己已巳的三天里,确是见到当地的小孩若无其事地跑来逗猫、看鱼,但院中的结构仍引起我的好奇,“三坊一照壁”是白族民居的普遍形制,“坊”是天井三面的“两层三间”的正房和厢房,照壁则是正面墙上有装饰的高墙。这样的形式背后,有其实际功能。比如,大理风大,照壁以挡风为用,且古时二层的房间用来储物,恰能运用大风和西晒驱赶潮湿。改为民宿后,二楼住人,客人又喜好晒太阳,如何在酒瓶里装进新酒?
“那是本地工匠的馈赠。”田飞告诉我,保暖问题在旧木屋更多靠电热毯,而咖啡馆所在的二层小楼却可以用传统方式来解决。他发现老木匠有自己的“口诀”,建房标准都是代代口传心授。“那时木匠都转去做泥水匠,我请他们过来用土法盖房子,咖啡馆的二层比例按他们说的来,只是换成露台的形式,用了水泥材料。而在二层室内,传统的夯土有五六十厘米厚,冬暖夏凉,本身就能解决问题,还能在墙上直接掏个洞放灯。墙面就用最普通的茅草拌上石灰,还有杀菌的作用。”
干活时,田飞发现这些本地木匠与城里的工人不同,自尊心很强,宁可撂挑子不干,也容不得挨说。他不懂当地建筑,就自己当小工,帮着和泥,和他们一起干,他不光不觉得委屈,却对老木匠越来越尊敬。“前些日子,我们这里刚走了一位老木匠。我们这里所有的门窗都是斗榫结构,有一处最靠边的门,我想省事一些,用合页的方法来做就行了。老木匠硬说自己不会做,死活不再干了。”田飞不无遗憾,“合页门钉一下就行了,他哪里是不会呢?”
当地工匠在一家民宿的房顶上除草、刷漆
田飞记得,初到村里时,村民好奇,建房时围在他旁边看,后来田飞也融入他们,村里修路也会和村民聚在一起看,唠叨家常。与在北京的艺术家村时,自己写书、妻子作画,同外界隔绝的生活相去甚远。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在村里尝试不同的可能性,在房东家里开设新客栈,又谋划员工入股,租院办客栈。在与村民的攀谈中,他又机缘巧合地改变了喜洲的民间工艺,那也是他被称为“田老师”的原因。
(感谢李太雄、毛先生、乔阳对本文的大力帮助,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02期,原标题为《喜洲:古镇的午后》)
大家都在看
⊙文章版权归《三联生活周刊》所有,欢迎转发到朋友圈,转载请联系后台。
|
|

 |关于我们|小黑屋|手机访问|Archiver|曲靖论坛
( 滇ICP备12002555号 )|网站地图
|关于我们|小黑屋|手机访问|Archiver|曲靖论坛
( 滇ICP备12002555号 )|网站地图 滇公网安备53032402000512号
本站已运行天
滇公网安备53032402000512号
本站已运行天